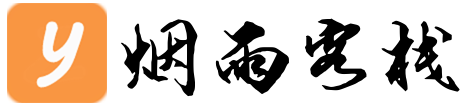村里有一座老庙,名曰“东岳殿”,祭奉的神灵是黄飞虎。虽是神庙,感觉却阴森,当然也许部分原因是源于自身对鬼神的惧怕。庙堂里供着几尊油漆残缺的佛像,潦草的大脸长眉,虽和善,却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慈悲。堂内的幡带垮塌塌地垂着,香炉是沉寂的,只在十五初一时,才集中焚上一两炉,香烟推挤着升上去。最碜人的是壁上用黑红墨水画的阴曹地府,满墙的散发与鲜血,编排出荒诞奇异的惨状,大概是下地狱后的各种极刑,看了令人浑身寒浸浸。
这样的地方,我是不大去的,除了偶尔去看采茶戏。
殿里有个临门的阁楼,围了圈镂空扶栏,四面通亮,可以清楚地看到里头景致,是现成的好戏台。农闲时分,遇有人家嫁娶,或者节庆,总会请村里的戏班在此唱上一场。三两下胡弦拉过去,锣钹昌嗯昌嗯敲响,抹了两块长胭脂的旦角便踢踢蹋蹋走出来,甩了两下八角巾,一拧身子一睁眼,顿了顿,嘬圆嘴巴,细细利利唱开来。
常见的剧目是《瞧妹子》,或者《采茶歌》,更多时会唱《戏妻》,粗野泼辣的调情,看得台下哄堂大笑。
采茶戏是武宁本地小戏,起源于民间采茶歌。清代李调元《粤东笔记》中记载:“岁之正月,饰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燃一宝灯,罩以绛纱,明絙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这便是为最初的采茶戏了。后来经多方演变,在歌里加入或雅或俗的动作,边歌边舞,随唱随跳,方成这样质朴大方的民间艺术。
采茶戏里的唱词用的都是道地土话,粗野真实,风味天然。唱戏的大都本村农人,非专业科班出身,这点与周作人家乡的目连戏班子很相像,“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他们的戏服一向寒碜破旧,没有里袍,只一件套褂,再加上一顶脱珠掉线的冠帽,便是全部行头了。但因了好兴致,还是唱得欢实。
村里娱乐向来贫乏,村民们无甚可看,于是对这村头土戏也将就着热爱起来。一听要唱戏,家家便好一阵兴奋。日间早早收了工,回家煮饭,梳洗,挑出见客的好衣裳来穿上。
火烧云还在天边霍霍燃着的时候,东家婶子就收拾妥贴,掇着一条板凳,走过西家娘的院子,高声喊:“去看戏喽!”
“好啊,我洗将碗就来咧!”西家娘揉搓完那一锅钵碗,把手在围裙上揩了揩,换上一件溜平的衫子,沾了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服贴,在黯仄仄的镜里照了照,很满意,然后拉上汉子一块出了门。
在路上遇见几伙本村的姑娌,打扮得花团锦簇,相互绞着胳膊,嘁嘁喳喳地走过去,引得路旁小伙儿纷纷侧目。卖杂食的老人早早地坐在庙门口,篮子里装满了瓜子话梅花生,也有卖油糕和汽水的,守着另一个门樽坐着。戏还没开场,人却是多起来,三五成群地唠嗑,说些村头村角的各种杂事,以及田地的收成。
阴冷的庙宇此时热闹起来,几盏一百支光的电灯咯嗒一声拉亮了,黄灼灼的灯光扑上庙堂,往日里结满尘灰的巾幡蒲团,忽然堂皇华丽。阁楼的戏台上搭了张红色八仙桌,搁着烛台针篓,桌边是两张旧太师椅,四平八稳的象是波澜不惊的民间岁月。
有人说:“要唱了,要唱了!”大伙急忙把板凳掇端正,坐好,齐刷刷拉长脖子,等了半天,锣钹声总算一粒粒滚出来,一个穿绿绸衫的胖女人划着双手出了场,把八角巾抖了几朵花,然后颠颠地转了圈,唱:“奴家王氏女,配夫张三郎,奴夫赌钱一去未还乡……”
拈着八角巾的手在胸前环绕一下,一点,继续往下唱:“明灯高挂起,照见象牙床,象牙床上未见我张三郎;鼓敲一更深,望夫不归程,闲坐无事我沏麻打鞋底……”
然后,她从篓里翻出鞋底,在空气里嘶拉嘶拉扯着线,线太紧,她便往下用劲一扯,脸上脂肪跟着一抖擞,继续扯,便继续抖。
灯快灭时,她矮壮邋遢的丈夫回来了,大头歪嘴吊肩膀,画着白夹鼻,穿着肥筒裤,白褶裙,盘着双腿抖来抖去走“矮子步”,粗野滑稽,言语也多是夸张可笑的直白,直令观众哈哈大笑。妻见丈夫回来,便开始吵架,男人自知理亏,就涎皮涎脸地对其逗乐调情。“回到我的窝,看到我老婆,老婆赛过月里的嫦娥;不但可以看,而且可以摸……”
说到露骨时,一旁有看戏的妇人轻轻啐着:“这打短命的!”仿佛她就是那张三郎的妻,也被骚鼓得脸红心跳。
壁上地府极刑图中的小鬼,仿佛融了几许人间喜色,于是多了些温和,消了几分阴冷。佛像森然的金脸在黄滟滟的灯光下熠熠生辉,竟有几分圆满详和。
接着上来两个年轻的小旦,绞着实沉的大辫,穿着菜青的衫裙,唱《采茶歌》,“春日采茶春日长,白白茶花满路旁;大姊回家报二姊,头茶不比晚茶香……”眼睛边唱边流,流到台下青年后生的脸上,羞怯地滞了一滞,收了回来,过会儿又递出去,反复再三。台下的后生们大声叫好,也是兴陶陶,认为这是全场最好的一折戏。
夜色一点点暗下去,远处村落亮起零星的灯火,晚风吹过来,如姑娘的清凉酥手,轻抚着寸寸肌肤。村民们一边听着抑扬顿挫的戏文,一边剥着些坚果,喝着汽水,其中情致也算得上缱绻了。
接着,又演了几出,有一出是《韩湘子戏妻》,讲的是韩湘子变了个丑八怪模样的和尚,来调戏自己的夫人,也是笑料百出。唱了半日,场上人渐少起来。后生们走到田间麦垛后面,买了包瓜子贿赂伢崽,让其传话给相中的姑娘来幽会。孩子们传好话,拿着瓜子毕毕剥剥吃了阵,又看了会儿小丑扭屁股,但实在消化不了这冗长的戏文,就到别处打闹去了。殿里此时余下的都是年长者,稀稀朗朗坐着,仍听得津津有味,情到浓时,甚至有人掏了帕子来揩眼睛。
若不是夜晚星斜,这戏还要不停不休地唱下去,无奈次日都有活计要忙,于是意犹未尽地谢幕,卸了妆,收拾行头回家。一路无话,内心里都有微酣的饱足,回头看看东岳殿的阑珊灯光,慢慢湮化,渐化成一个未央宫渺,浮在秋夜皎皎的月色中。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一句:“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却自有他的风致。”正说中了我的意思。采茶戏无疑就是如此,不得禁锢于室,本就是来源于山头郊野的农活助兴艺术,在旷野方能活灵活现,才能唱出其铿锵泼实,而又袅袅流连的真韵。
我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东岳殿了,偶尔回家,也不会特地去看。前不久听说已被拆除,内心一阵放松和遗憾。放松的是一直以来紧绷着的恐惧;遗憾的是再也见不到那秋夜时分在东岳殿的小戏台上演的采茶戏了。
文/周冲
本文来自作者:南岸青栀,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yinn.net/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