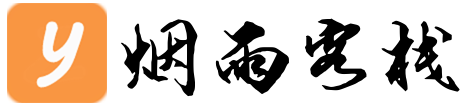◎云也退
将近一百年前,当一场流血漂橹的世界大战终告一段落时,瓦尔特·本雅明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读着报纸,坐火车到处旅行,并尝试用笔来写下感受。很多年过去,他终于有了一点领悟:人的经验——他说——在战争之后跌至了新的低谷。
“将士们从战场回归,个个沉默寡言,可交流的经验不是更丰富而是更匮乏,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十年后,描写战争的书籍涌现,可里面倾泻而出的内容绝不是口口相传的经验,这不足为奇。因为经验从未像今天这样惨遭挫折:战略的经验为战术性的奴役所取代,经济经验为通货膨胀所取代……”
他说得没错。关于一战经验的文学作品,能被列入经典殿堂的大概只有1929年出版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此外也就是少数的回忆录。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人却普遍失语,没有经验可以传达。这是为什么?本雅明分析说,是因为人们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被报纸以“消息”填补了故事留出的空白。消息永远是“不证自明”的,它的叙述往往并不准确,至少不比商业传媒尚未问世时的那些有限的报道准确,可是,“它听起来非得合情合理不可”,正是凭这一点,报纸和其他消息源获得了大众读者,而读者原本都是故事的听众。
本雅明是个奇人。他年少时的一件事,可以见出这人的奇特。大约20岁的时候,他感到终于摆脱了学校教育,也可以不再受家长的管束了。他的家境不错,文化高,还有艺术品收藏,他妈妈在那年过生日时请了许多有教养的人士过来,当人们正在兴头上时,本雅明走上前,大声献读一篇他新写的短篇小说。这件事引起了在场大人们怎样的反应,已不得而知了,但小说文本保留了下来。这是一个没什么情节的小说,写一个大学生从瑞士坐火车回学校,在途中,在无聊的驱动下,他对周围人和事物的观察。他没有跟任何人争论,这故事里的张力可以说就源于那种年轻男人的性挫折、性苦闷和无聊。
这个小说的题目叫《静物故事》。如果联系本雅明后来对新技术、新交通工具、城市景观等等的关注,或许能在其中读出不少端倪,似乎年轻的主人公在这无所事事的路上一天里,感受到了不由分说飞驰的火车给他的青春施加的压力。本雅明不到五十岁时就在二战的血雨腥风中自杀身亡,生前从未把他的小说作品出版过。他是一位写散文、写格言警句、写思想片断、写宣言、写书评的大师,大多数作品里的他都是一个自由而深刻的批评家,这种批评气质也渗透在了他写的故事里,克制、沉着,完全不追求19世纪经典小说所追求的情节。
可是,本雅明却又如此地看重故事。他几乎视故事为神圣。如果说,一群人会因为长期生活在一片土地,分工生产、繁衍后代,从而拥有了可识别的共同特征和共同经验的话,那么故事就是这些人在共同生活中,彼此交流各自的经验而得的产物。这种经验的价值,随着大战的发生而下降了。《讲故事的人》这篇著名散文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写的,它的副标题“论尼古拉·列斯科夫”——这分明是一篇论一位19世纪俄国作家的文章,可显然,本雅明的醉翁之意远远不在于酒。
他说,故事和历史学有着同一个发源地,那就是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英文的“历史”一词“history”包含了“story”(甚至可以解释为his-story,即“男人的故事”),而本雅明所用的德语中“历史(storia)”也兼有“故事”的意思。——真正的故事,并不只是一种口头文学传统,而是要坚持一种“叙述幅度”,它立足于一个地点,一个时间,要集中起一组条件来使它有资格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并获得反响。讲故事的人首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听众,他可以从渗透了对话、劳动、工作和死亡的人类生活中汲取内容,并且把一代代人流传下来的东西分享出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生命的灯芯被故事的温和火焰完全吞噬在其中”。此外,故事也会提供建议,无论公开还是隐蔽的,故事都要包含有用的线索:可以是提供一种生活智慧,也可以是给出某个技能,比如用卷纸卷好一支烟。
本雅明自己的小说示范了一种全然非道德化的写作。读过他的一则“准小说”《谈谈赌博》后,就会发现他并不真正关心赌博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好坏。就在《讲故事的人》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的1935年,他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又一篇小说,它讲的是一个从一位著名的杂耍艺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而这个艺人讲的则是他自己的一个同行在为土耳其苏丹表演时的一次冒险经历。看起来,这正是本雅明心目中“故事”的本来样子:它发源于一些从事相似的生活的人,无关道德,却拉近了说者和听者的距离,并拓展了听者对世界的感知。
这篇题为《拉斯泰利讲故事》小说的结尾也落到了“故事”上。这位杂耍艺人总结道:“我们这个行当并不是昨天才诞生的,我们有自己的故事——或至少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故事。”杂耍艺人,土耳其苏丹,这类角色都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所以“讲故事”的传统在此体现为一种过去式,本雅明并不试图挽救它的式微,正如他的第一篇小说所示,他看到典型的现代人情绪是孤独的、失意、长时间处于无聊状态下的。在《讲故事的人》中,他也说到了无聊,他说那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之鸟”——他充分拥抱无聊,并将它升华为一种精神。
关于“消息”取代“故事”的论断,以及关于无聊状态的切身体验,在21世纪的开端就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事实:纸媒最后的黄金期过后,获取消息的方式简便到极点,因而人被成千上万的图文消息淹没,以消息来缓和无聊的结果是在无聊中陷得越来越深——有谁不曾在几十分钟耗尽视力的浏览之后感到无聊过?如果没有感受到,那是因为他迅速进入了下一个打发无聊的活动之中,或者干脆就这么睡了过去。
本雅明的典型的文风是态度暧昧的,浮现着一层忧郁的色彩,但灼痛性的见解还是时不常地出现。他说到了死亡:讲故事的人之所以能讲述一切,都是源于死亡的许可。他神秘地表示,讲故事的人向死亡借来了权威。
想想是真对。20世纪之前的人谈论死者时多么从容,像是那个杂耍艺人把故事同他的行业联系起来,而他的讲述,自己也成了本雅明这位叙事人眼里的“故事”。“故”即“过去的”,“故事”即“过去的事”,叙述它们就是宣告了生与死、今与昔的互相包含。“过去,没有一户住宅,没有一个房间,是没有死过人的”,所以生者一直和死者在一起,基于对人的必死性的朝夕见证,他们讲起了故事。可是,现代的城市化社会的运转,是建立在把生死分开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被植入了对死亡避之唯恐不及的潜意识,并用卫生洁具、药品和消毒手段驱散死亡的端倪,把重病临终人士交由疗养院和医院关怀,自己则尽量眼不见为净。死亡这一所有人共同经历的生活被压抑住了,因而也丧失了权威。
上海有很多保留下来的老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往往都能讲些故事:哪位民国时期的大亨曾在这里住过,哪位文坛名流在窗下走过,他们的后代流落到了何方,等等。住老房子的人,不会像住公寓房的人一样,三五句话后就回到房子的价格,物业的水平。“故事”是他们生活在这里的理由。
可是而今,他们的很多人被困在了老房子里,不能出来。在深夜时分,有的房子里传出了男人的尖叫。死亡的气息,总会趁夜浮现出来,那些已故的人不再是房间里永恒的居民,而变成了某种召唤师一样的存在。如果本雅明再世,来到上海,他会说些什么?眼下的时空是彻底割裂的,丧失了必要的见证。共同生活的经验彻底丧失,焦躁的灵魂四散在各家室内,暗淡并麻木。除了吃饱后坐待天明,我们真的需要想一想,该怎样为无法叙说的经历寻找最合适的叙说。
链接:https://www.yyinn.net/197840.html
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自行上传,本网站不拥有所有权,也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果您发现有涉嫌版权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www.yyinn@163.com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