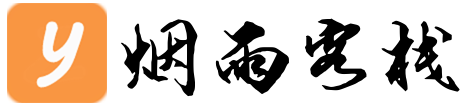沈齐的生活一直隐蔽在那间漆黑的、灰色窗帘几乎没有拉开过的卧室里,靠着二伯提供的一条网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生活。因为皮肤烧伤无法出汗,他卧室里的空调24小时都开着,「时间长了,他的空调开得像炸弹一样。」
在没有外卖软件的那些年,他偶尔会出门吃饭,也会用电话打给附近的饭店点餐,或者去便利店买点食品将就一下——后来他不再出门,也不随意开门。
沈齐彻底关闭了那扇通往外部现实世界的大门。
[1]
住在这栋楼里的人都知道,脏乱的203室住着一个隐居的男孩。
首先不是脏,而是一股混杂了食物、排泄物之后腐烂、发酵的熏人气味——它流窜在楼道与楼梯之间,一直传到5层,202室的朱阿姨声称自己得戴上口罩才敢出门。脏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没人透过那扇布满黑色污渍的铁门真正窥得屋里的景象,但门外那些讨人厌的生物就说明了一切——苍蝇、蚊子、不知名的黑色小飞虫聚在门外,矿泉水瓶子大小的老鼠们排着队从墙上的铁管跑过,一大滩长长、圆圆、黑黑的老鼠屎黏在楼道的水泥地面上。202室的上一任业主闲置房子一段时间后回家取东西,拉开抽屉,看到一窝光不溜秋的老鼠幼崽。
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明白,老鼠是被屋子里堆得齐腰高、连门都堵住的垃圾引诱而来,它们包括装着食物残渣的塑料袋子、食品包装袋、用过的纸巾,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粪便——粪便堆得比马桶还要高,连塑料袋子里都装着一些。
独居在此的男孩叫沈齐,据推测,他今年应该25岁。「他小时候我看见过,后来就没见过了。」小区坐落在上海中心城区,门口一间营业了二十多年的理发店老板这样告诉我。住在沈齐楼上的503室吴大爷看着沈齐从小长大,但上一次见他也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202室的朱阿姨有一次听到沈齐的二伯在用力敲门,「『沈齐,沈齐,你给我开门』」,但门始终没有开。居委会也毫无办法,「你在外面喊破嗓子,他也不睬你的。」他们只能不定期打电话给他,以确保他在拥有2400万人口的上海的中心城区里还活着。
8月的某个星期,我每天都去到沈齐所住的楼里等候,希望获得一个和他见面的机会。没有人确定自己一定能认出他来,若干人的回忆也只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大概一米七的个子(如果他最近几年没有长高的话),鼻子挺挺的,上一次他被见到的时候,头发已经齐腰长了,像一头黑牦牛似地披散着,遮住了脸颊两侧的白色疤痕。直到离开那天,我还是没有见到沈齐,但也并非毫无收获——一天傍晚6点多,天已经有些昏暗,我刚走到二楼楼梯的半截处,一只白白胖胖的手从203室里伸出来拿走了外卖袋子,旋即关上了门。
关于203室男孩,我们所获得的是一些经人们回忆后拼凑得成的故事。
其中一件事发生于13年前:
「他爸爸烧死他妈妈跟外婆,一家子三口人,爸爸妈妈死掉了,外婆死掉了,孩子活下来了。」202室的朱阿姨如此简练地告诉每一位来访者。对于这栋楼的老住户来说,203室夫妻打架摔东西、找110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503室的吴大爷回忆,火灾那天,「他爸爸把10公升的那个汽油桶呀点着了,玻璃都爆了。从2楼一直到6楼,都是黑的烟,像那个烧火的炉灶一样的。」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火灾后的最初几年:
火灾那年,沈齐12岁,爷爷成为他的法定监护人。这位老人不识字,走路佝偻着背,每天像蜗牛一样拖着沉重的身躯步行约5公里来给沈齐「烧烧饭」。尽管沈齐烧伤了50%的面积,被鉴定为「肢体三级残疾」,但那会儿他三天两头也出门,大多时候是到附近的公园和大爷们下象棋。公园里密布着高耸的梧桐树,四周都是虫鸣鸟叫,直到现在,那里还有人记得沈齐,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说,「那小孩刚来的时候不会下棋,看久了就会了,下得还挺好的。」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事情就走向了无法挽救的境地:
2015年左右,爷爷病重住院,需要插管治疗,不能再来照顾沈齐。但有人记得是2010年,那时全上海都在欢庆世博会,而沈齐已经不大出门,敲门也不怎么理睬。有人在2012年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已经有点长了,开门收东西时只会如此回应,「哦。」还有人在四五年前非常偶然地在室外见过他,但次数只有可怜的一次。之后,他几乎不再出门。
 沈齐所在居民楼楼道窗户
沈齐所在居民楼楼道窗户
[2]
8月1日一则上海电视台播报的新闻让沈齐又从这座城市中浮现了出来。
新闻记录了居委会在一个多星期前清理沈齐所住203室垃圾的过程:4位清洁工人全副武装,雨衣、口罩、手套、鞋套,他们从早上九点清理到下午三点,足足装了20大袋垃圾,一卡车都装不下。解说词写着:「独居青年足不出户,家中垃圾堆积成山。老鼠苍蝇和蚊子,臭气熏天令人作呕。四邻遭殃苦不堪言,前去敲门都没反应。小伙今年二十五,明明在家就是不露面……炎炎夏日空调坏了,这才让居委进门维修,任你维修任你清扫,我自闭门(卧室门)岿然不动。」
 从203清扫出的垃圾,图源看看新闻
从203清扫出的垃圾,图源看看新闻
「我的第一感觉是你们怎么想起他来了?你们怎么开始关心他了?」68岁的肖秀全看到新闻后感受复杂,他从1998年起在沈齐所在小区担任居委会书记,直到2014年才卸任,和沈齐一家是老熟人。他回忆,沈齐的爸爸是所谓的「上门女婿」,无业,绰号「枪手」。妈妈则是外婆唯一的养女,身体状况不太好。一家人要靠外婆的退休金过活。沈齐是外婆带大的,从小和外婆住在同一个房间。
肖秀全曾给沈齐的爸爸安排过一份在小区门口穿绿马甲收废品的工作,没多久他就不干了,把活儿转给了别人,每个季度收1000块钱转让费,自己常端着装着茶水的雀巢咖啡玻璃罐,去一个今已拆掉的旧商店里搓麻将。
因为怀疑妻子外出工作后变心出轨,他们家三天两头都要吵架,肖秀全也开导过好几次,没有效果。肖秀全回忆,沈齐爸爸对外曾经撂过狠话,「要杀死他老婆,要烧掉什么东西,只留下小孩,这个事我听说过。」
当天,沈齐的爸爸提着刀准备去报复妻子的疑似出轨对象,没找着人,就气冲冲回了家。他先用刀捅死了妻子和岳母,接着点火,和她们抱在一起,在火中自杀了。火灾那天,距离这对夫妻到法院开庭协议离婚的日期只剩2天。
唯一的幸存者沈齐,在事发前被爸爸反锁进卫生间,肖秀全从公安方面的信息得知,妈妈和外婆的呼救声沈齐听得一清二楚。肖秀全拧着一张脸,靠在办公椅上,点了烟。「父亲杀母亲,这种场面,基本上在我们这个社会是罕见的,他受的创伤,受的痛苦,受的刺激,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正如肖秀全所预料的那样,12岁以前,沈齐是健康的,有礼数的,成绩优秀的。12岁以后,他是残疾的——烧伤了50%的面积,被鉴定为「肢体三级残疾」;自卑的——在路上,他总是低头靠边走,成为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辍学生。
公安局找到将近80岁的爷爷作为监护人——爷爷有5个儿子,沈齐的爸爸排老四。在此之前,两个家庭几乎没有来往。但仅凭一条理由就能断定,这位老人是沈齐最应该信赖的人:他不仅每天来给沈齐做饭,还会照顾沈齐收留的几只流浪猫和流浪狗。「爷爷好几次来都拿着个蛇皮袋,放那个蜂窝煤烧过后剩下的煤灰,再把煤灰铺在地上,猫不是要拉屎嘛,狗要拉屎嘛,它们拉在煤灰上,他再把这个垃圾清理一下,放在这个蛇皮袋里面倒掉。」503室的吴大爷目睹过这一切。
但沈齐和爷爷的关系并不融洽。肖秀全有一次登门,走到门口时听到沈齐喊了一声,「饭烧好了没呀?好了就走。」爷爷给肖秀全开了门,做完饭,垃圾收一收,就和肖秀全告别,「我走了啊,我走了啊,谢谢(你来看他)。」
爷爷向邻里倾诉过:「挺难过的,很累,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年纪大了,我也照顾不动了,我还要坚持着。」
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沈齐的爷爷从每天来一次,变成一周来两次,一周来一次,一个月来一次。2010年到2014年间,在居委会负责卫生工作的陈阿姨去沈齐家「小搞」过几次卫生,「大搞」则只有一次,「拉粪便的拉粪便,倒垃圾的倒垃圾,擦煤气灶的擦煤气灶,拖把我们手也捏不上去,太脏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外卖,厕所里粪便堆成山,厨房里还有吃完的牛奶盒子,他也不压扁了,一个一个方方正正地搭起来。」有一次打扫时,她还在另一房间里发现了一条不知道是猫还是狗的尸体。
到了2015年左右,沈齐21岁,爷爷病重住院,需要插管治疗——且不说照顾沈齐,他连自己都需要别人来照顾。
自此开始,关于沈齐的一切大多模糊不清,但只有一件事是确切的,那就是离开了爷爷的照顾,沈齐就彻底关闭了那扇通往外部现实世界的大门。二伯是目前唯一还在操心沈齐的亲人,尽管也有邻居声称,他已经有好几年不来了。有时二伯上门,沈齐也不开门。301室的吴阿姨说,「后来他二伯也不高兴了,他说我管不了。」
几乎是与爷爷病重同一时间,沈齐开始点起了外卖——在没有外卖软件的那些年,他偶尔会出门吃饭,也会用电话打给附近的饭店点餐,或者去便利店买点食品将就一下——后来他不再出门,也不随意开门。301室的吴阿姨说,「他也不要别人管,他说什么,我成年人了,我要你们管干嘛,我不要你们管。」

沈齐所在的居民楼
[3]
沈齐的生活一直隐蔽在那间漆黑的、灰色窗帘几乎没有拉开过的卧室里。靠着二伯提供的一条网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他叫外卖、网购、打游戏——一个从二伯处辗转传出的消息称,他在游戏里不断积分刷装备,再把装备卖了挣钱。因为皮肤烧伤无法出汗,他卧室里的空调24小时都开着,「时间长了,他的空调开得像炸弹一样。」他并不需要交水电费,街道工作人员曾出面让水电公司直接免去了所有费用。他每月能领到包含低保在内的1500元补助金——原先居委会还能借此机会和他见上一面,但2016年起,补助金从现金发放改成了线上转账。
生活就此彻底失序,他不再出门,所有装着食物残渣的外卖袋子都丢在屋里,马桶不知什么原因一次又一次地堵塞了——居委会至少给他换过两次马桶——后来沈齐也就不在卫生间里上厕所了,202室的朱阿姨转述了一位快递员的经历,他去203室敲门送快递,屋里的人让他直接推门进来,一进门,发现沈齐正蹲在地上大便。
即便有如此多不同寻常的状况发生,但人们还是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钱。现任居委会主任韦国英有好几年没见过沈齐,新闻出来后,她接待了数十家媒体,耐心渐渐被消磨光了。她拒绝了我的采访,「你们现在的媒体,就是采访报道,你问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是经济,钱,还有他生活的改善。」
新闻爆出后,二伯来找沈齐商量过工作的事,25岁了,是该考虑未来如何养活自己了——二伯的工作是「烧锅炉」,那也只是一份勉强养家糊口的工作。沈齐对工作提出了这些要求:室内的,恒温的,工资四五千的。现任居委会书记周慧琼觉得他异想天开,「我们跟他讲,你这个情况,还是小学学历,根本不可能的。」
但没有人为沈齐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负起过责任。火灾发生时,他只有12岁,网上流传他当年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一,当我致电这所中学的校长时,他告诉我学校只有高中。通过多方验证,可以确定沈齐的母校是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现改名「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但因为暑假,我们没能找到学校老师能帮忙查证当年的信息。
沈齐曾告诉肖秀全,他想继续读书。肖秀全声称给他找到了学校,但这个希望很快被沈齐的家人浇灭——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住宿,空调,按摩。「我们街道社会发展科是管教育的,可能跟学校联系了……但哪有这样的学校,就不了了之了。」
2013年左右,居委会带过一次街道医院的心理医生上门,但沈齐只是签字收钱,没有回应心理医生的提问,周慧琼说,「心理医生也说了,光我一个人说没用的,我们要交流的。」今年夏天清理垃圾的新闻出来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组织了一个心理小组,大家开了次会,结论仍是,只要小沈不沟通,那就没辙。
只有肖秀全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愧疚,「这小孩真的,有时讲讲心里很痛,当时没有对这个小孩进行一系列心灵上的抢救措施。」
202室的朱阿姨同样对沈齐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但她也茫然于自己的境况。去年5月,居委会刚从沈齐家拉出一卡车垃圾,一个月后,67岁的朱阿姨就搬来了,她以500万的价格买下了55平米的202室。直到装修时发现老鼠从门前溜过,她才知道自己倒了大霉。住进来没几个月,她又查出了病症,直到现在还在化疗中。她整天郁闷地待在门窗紧闭的家里,两台空气净化器工作着。她不出门,也不敢让亲朋来串门。她有时也纳闷,204室怎么也住着一位奇怪的独居男士,他看起来40岁出头,似乎也不总是出门,有一回他开门时,朱阿姨瞄见他家竟然出其的干净。
有邻居在接受采访时厉声谴责沈齐:「居委太纵容他了,他空调坏掉了,可以拿这个要挟他的,拿点手段出来啊,把交换条件写好,你只要把垃圾拿出来,我们不要你倒,摆在门口,我们有人会给你收垃圾,不要你分类。你把家里搞干净就行了,你把你的饭盒拿出来,大小便冲进马桶,你家里就不会脏。」
没人能接受,一个能使手机能耍电脑的25岁成年人,怎么还能在秩序井然的现实社会里拥有失控的豁免权,他必须干净,不能影响他人,还得找份工作。在我的采访中,只有一位年轻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为如此生活了13年的沈齐感到赞叹,「他活到现在也是不容易。」
门外是另一个世界。在热闹又舒适的上海中心城区,粉色外墙的居民楼一栋挨着一栋,清晨5点就有人在跑步,路上随意可见菜市场、餐馆、24小时便利店。这里属于漕河泾街道,一条5公里长的漕河泾港穿过街区。过去的漕河泾是一个百年老镇,一座拥有湿地和游乐园的公园就在沈齐家对街,出门走300多米就是沈齐曾经就读过的小学。
四五年前,一个深夜,503室的吴大爷下楼丢垃圾,他看到2楼楼道里站着一个黑影,那个黑影驻足在透着微光的窗户前。透过红棕色的窗框往外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但一听到脚步声,那个黑影迅速转身,又躲进孤独的203室。
(沈齐、肖秀全为化名)

链接:https://www.yyinn.net/2959.html
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自行上传,本网站不拥有所有权,也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果您发现有涉嫌版权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www.yyinn@163.com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