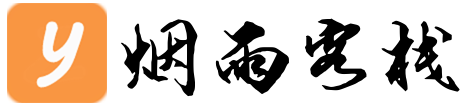我已经七天水米未进了,可我还活着。
这副干枯的身躯奄奄一息,却又不能断气,像一棵死在冬天的树,它闻得到风里的花香,却再不能发芽。
春寒料峭,我躺在被子里,清醒的感觉到生命一点点的流失,被窝里只剩下若有若无的温度。儿女们常来看我,轮番登场。那天,从医院出来,医生告诉他们,我撑不到天明。可是老天爷,又过了七天,我还活着。我知道他们每次进来,都是想看看我有没有死。我的寿衣都做好了。我的棺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只等我咽气。
在这七天,村庄和麦田沉睡的时候,我有点迷糊,分不清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幻,回忆乘着黑夜与沉寂飘浮在我的眼前……
第一天夜里,我的孩子们在外间都休息了。老伴睡在隔壁的小床上,她又开始怕我了。
外间忽然下起了大雨,雨声哗哗。我听到老伴均匀的呼吸声。她睡的那么香,我有点羡慕。我也想睡着,然后再也不睁开眼睛。合上眼,我似乎睡着了。却仿佛看见这样的画面:老伴在跟人在院子里说话,她说:“年轻时候那么明白的一个人,怎么老了也糊涂了。他想活啊,但是得的是啥病?那是绝症。”她嘴角有唾沫飞出,斜着眼,她划拉着双手继续说:“天天在我身边龇牙咧嘴,疼的哼哼唧唧,吃什么都吃不下。我早晚也被他折腾死。”她此刻的眼神闪着世故的精光,她的嘴角里蹦出的话让中午的阳光都有些寒凉。我现在病倒,再也不会打骂她了,甚至使脸色都没有力气了,她有点兴奋了,似乎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高高的抬起了头。蠢婆娘,难道你不知道,我死了你的日子只会更艰难么?
如果有一天,你即将死去,身边有人不舍得你离开。那么,你之前一定待他很好。看到他,你走的也会心安吧。
的确,我待她不好。所以,她说这些话我不怪她。
当年,我是个帅小伙时,也颇有家资,还读书识字,附近的姑娘随我挑。我却偏偏挑中了她,我的第一任妻子,她体量苗条,面庞姣好,皮肤白嫩。我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虽然对她冰冰冷冷,但也给了她我能给的一丝热情。
也是这样一个大雨的天气,我刚好走到村西头,就在大明家屋檐下避雨,在哗哗的雨声里,我听到我妻子的声音,那声音哼哼唧唧婉转缭绕。我的血一下子冲到头上,我踢开了门,赫然发现那对狗男女交叠的身子。
我把大明揍了一顿,把她拖回家,吊起来打了一顿。打的时候,她威胁我,说如果接着打她她会让大明杀了我。可是我又打了她半个小时,大明也没有出现。后来,她一直不停的求我,求我不要打了。我将她打了个半死,淫妇,这就是背叛我的代价。
我当然不会再要她,跟她离了婚。我是个洁癖的人。在农村,你找不到比我家院子利落的,也找不到比我家茅房更干净的。一想到她的脏身子曾睡在我的被窝里,我就恶心。我把被子通通烧了。
后来她嫁给了大明,还搬家住到我家隔壁,我真后悔当时没把她打死。不过她死的很早,我都忘了是哪一年。
我不想再婚。可是母亲却不愿意。我出了这样的丑事,方圆十里都没有人愿意嫁给我了。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嫁我的姑娘,她又黑又矮,还比我大两岁……我不喜欢,不过我想,这样总安全了。
可婚后我发现她性格粗鄙,邋遢,爱吃,贪小便宜,不懂规矩,没脑子乱说话,愚蠢又世故。我母亲当年是富家小姐,总觉得我妻子粗俗不堪。她蠢笨的时候常常惹我母亲生气,我便打她。但她居然屡教不改,于是我更加狠的打她,拿鞭子抽她。她怕我,但她一辈子都改不掉。
六十岁之后,这状况才有所改善。这样粗俗的她,绣花的手艺却很好,十里八乡的闻名。她常常剪一些花样子,拿去集市上卖。她不会骑自行车,又不舍得坐车,都是步行七八里地去赶集。不知道哪天起,我开始骑车载她去赶集。渐渐的,还帮她批发绣线帮她一起卖。中午,我们老两口一起回来后,我整理被弄乱的绣线,她静静的戴着老花镜开始剪纸。我们家院墙不高,院外是一条小河,河那边是一片麦田,故而无遮无拦。傍晚,阳光洒下来,她背对着夕阳坐在院子里,一丝不苟。剪纸是她一生的骄傲,她也经常自夸。虽然偶尔我还是会对她吹胡子瞪眼,不过,已经没有拳脚相向了。
雨顺着房檐滴答滴答的敲着,像在奏一首安魂曲。我多睡一会儿吧,让我在睡眠里死去,那里没有痛苦与荒凉……
第二天,我睁开眼,看到了我熟悉的房间,我还没有死。每个人的脚步声都让我心烦,我觉得他们来看我都不是真心,我闭上眼睛,对谁都不看一眼。夜里,是老三守夜。他在我的床前放个小躺椅,窝在那里似乎睡着了。他的呼吸声很轻,轻到你以为他也死了。
几个月前,我已经病的厉害,老三陪我去北京看病,看了半个月,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你的肠道里已经被肿瘤堵死了,就算喝水也很难流下去。”化疗的时候,我难受的浑身颤栗,牙关咬紧,我没料到此生还要受这样的罪。可我想活着,像以往那样,在我的院子里晒太阳,到我的田里看庄稼。可是老三却说:“家里等着我回去给儿子办婚礼,我先回去了,你要不回去你就自己待在这……”
我瞪着他,看到他的灵魂里,你忘了我以前是怎样对你的么?你难道不会有老的那天嚒?
他们小的时候,所有的儿子都很强壮,唯有老三,多病多灾,为人又灵巧会说话,办事稳当,我就格外关心他。他有常年的慢性胃病,我经常留心哪里有好的医生,他的饮食也格外照顾。那会儿家里做生意,我都是让老大老二去到处卖货,他就留在家里做最轻松的活计。给他娶媳妇,我千挑万选,要长得周正,要有头脑,要会过日子。他的媳妇是我和老伴都看得上眼的,给聘礼时候也很舍得。虽然和老二家房屋挨着,我还是给他盖了好很多的房子。分田的时候,把他家田地选在我的田附近,以便可以照应他。分家的时候,把家里的唯一的拖拉机分给了他。为这事,老大那个蠢货和他那个笨老婆很生气,觉得我偏心,将我打了一顿,从此我全当没他这个儿子。
唉,直到现在老大也没有来看我一眼。
老二家就分到一个柜子,那还是我母亲嫁过来时候的嫁妆。我从小就不待见他,每次看到他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遗传了我和妻子两个人的缺点,长得丑,没脑子,还暴脾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十八岁时,我给他三百块钱叫他去学糕点,他去学了一个月,全花完了,回来时说没钱了。我解开皮带将他抽了一顿,边抽变骂:“你个败家子,三百块,老子给你预防突发事件的,你居然全花完了。办什么事你能靠谱点?”不过,他的学习成绩还算有点用,我雇人来造了个大炉子,我们就开始做果品。当年没什么竞争,我们也算赚了一笔钱,在村里也算首富了。
可是老二自己出去单干的时候,却连炉子都造不好,果品不是烤糊就是夹生,赔了精光。直到现在他依然一事无成,就连我的医药费他都拿不出。他果然没出息,我没看错。他表达孝心的方式就是天天来看我。但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半月前他又出门闯荡去了,这不,听说我不行了,又得急吼吼的往家赶,不知道还能不能见我最后一面。
第三夜,我虚弱的睁不开眼睛,可我感觉得到是老四在守夜,他已经胖的走路都喘气,他躺在床边的小躺椅上时,我觉得躺椅要塌了。他是我最看重的小儿子,他长得好,随我,也灵活懂变通,办事最靠谱。不像老二那个死脑筋死要面子活受罪,他不在意面子只在意里子,在村里人称铁公鸡,一毛不拔。
我送他去学厨师,他学的还不错,但是回来居然开始说普通话,三天还改不过来,我给他照嘴一坡鞋,打的他嘴角流血。可他硬着脖子让我打,拒不认错。不过,打归打,我还是张罗着给他盖了全村最好的房子,娶隔壁村最美的姑娘。他结婚后,我们老两口跟着他们住,但是矛盾越来越多,他的丈母娘离的近,一听说小两口拌嘴就来主持大局,生怕自己女儿吃亏,让人不得安生。我决定搬出来,老四却大声嚷嚷:“如果你今天搬出去,以后你老了,俺哥出多少我出多少。你要是不搬出去,以后老了都算我的。”
我那时候身体还那么硬朗,还有一家之主的威风,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威胁。我于是在村东头的菜地里盖了三间小瓦房,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每天一起床,打开门就是我家的菜地,和老三家的菜园。天气晴朗的时候,就到地里走走,我照顾这田地,这庄稼,日子从未如此舒服和美。那时候老三在家做菜农,每天我也帮衬着。给黄瓜和豆角搭架子,留心每一种瓜果的长势,施肥的时间,一一提醒他。老天爷,他现在对着我的痛苦视而不见,却着急回去给儿子办喜事!
后来老四要在村里路边开餐馆,我的田有一块在那里,老三的也是。老三也想要我的田,老四也想要。我给了老四,因为老三越来越不像样,一年也不去看我几次,臂膀硬了,不需要老家伙了。老伴觉得给老四天经地义,因为老四要开饭馆,而老三要来干嘛?她于是偷偷去劝老三把他家的田也给老四。这蠢娘们!被老三媳妇骂了出来,从此,老三一家越来越不上我家门了。
既然已经选择了,我也就不多说了。老四当时在外地开餐馆,委托我和老伴帮他们建餐馆的房子。造房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老两口操心了一整年,房子终于造好。老四全家都回来了。他麻利的开始了他的餐馆,还有麻将馆。过年时候村里人都回来了,连邻村的人都来他这打麻将。我和老伴每次一有空就去帮老四的餐馆洗洗刷刷。唉……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不过,毕竟是老朽了,也没有多大的助益吧。所以我这次生病,老四也还是坚持哥哥们给多少钱他给多少。
罢了,我作的我受。
第四夜,我气若游丝,然而这游丝却那么顽强的继续着。女儿趴在我的床前睡着了,她瘦了很多。她的鬓角什么时候也这么多白发呢?我记得她小时候那么冰雪可爱,圆圆红红的脸蛋,晶亮的眼睛。像我有点优雅,又像他母亲有点粗野,于是显得那么有生命力,那么亭亭玉立。
她后来长大了,有很多人来说媒。十里之外的一个村里,有一个后生入得了她的眼。我一打听,原来这后生论起来还算我们亲戚,而且和我一个辈份,我就死活不同意。她比我还倔强,说:“我就是看上他了,你要是不同意,你以后就得找个比他好的给我。你找的到么?”此后她竟然绝食了三天。我拗不过,只好同意了。其实她眼光很不错,那个后生虽有些腼腆,却很忠厚老实,两人一个开朗一个可靠,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生意很不错。这些年他们都和和美美的,只是女婿后来从屋顶摔下来,腿脚从此不太能使力,家里的重活也得女儿来做了。这都是造化啊,谁也预料不到的。
老四说,他的餐馆少不了他,不能陪我去北京。我只能叫女儿陪我去北京治疗。现在只是拿钱来续命。我年轻时候辛辛苦苦攒下了一万块,多了不起啊,不过我一直不声张。此刻却连化疗的钱都不够支付。我的钱花完了,接下来该轮到儿子们兑钱了。这时,女儿跟哥哥们打电话后,跟医生说不想治疗了,让医生跟我说。医生老实的跟我说:“你的孩子跟我说了,不想继续治疗了。”
我说:“医生,你怎么能听孩子的话呢,现在的孩子哪有几个孝顺的?”我坚持治疗不肯回来。可是,女儿越来越疲惫,她跟我说:“爸,咱们先回家过年,年后再来。”我知道,年后再也不会来北京治疗了。。。余下的日子我不过等死罢了。
思绪飘飘荡荡,像一缕幽魂。我又想起春节的时候,我的一个孙子,他已经长大,工作了。他假期结束,快要回去上班了。我想,路那样远,我死了,他会回来看我最后一眼么?我为什么不趁孩子们都在家时候了断自己呢,那样大家都可以送我走了。可是老伴把农药都藏起来了,她说: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就不要在最后的时候再给孩子们添个坏名声吧。
那天孙儿要走,来看我,说:“爷爷要好好吃饭,明年回来我还要再看到你。”
我哭了起来。我快要死了,要成为泥土,我为什么还留恋活着呢?我只想这样日复一日的活下去。再看到我的麦田变成金黄色,我的菜园郁郁葱葱,我院子里的梨树果实累累。
第五夜,老二回来了,他守在我的床前。我看着他,第一次认真的端详他的脸。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他的孩子都变得臃肿或老态,而他,却显得最为年轻。是不是单纯的人比较不容易老?他的鬓角只有一点点白发,脸色虽黑却自带了股健康之色。他并不丑,只是他身上有我老伴的特征,而那些是我最讨厌的。他心地善良,但是他有着我的暴脾气,冲动起来又有着他母亲的愚钝。对这个家来说,他曾经任劳任怨,他的付出不比任何一个子女少,可我却没有给过他一个好脸色,这对他又何尝公平?
他从未抱怨我。也许心里怨吧,才会常年不回家……我要是当初对他好一点,他会不会是我最孝顺的孩子呢?我甚至不记得他最爱吃什么。好像是羊肉面,对,我记得他有一回吃羊肉面吃的一脸满足,笑的很开心。那大概是我三十岁时候,有一回家里做了羊肉面,一家子围在一起吃面条。儿子们比赛着谁吃的多,老二那天吃的最多。我以往都饮食有度,可是那天也破例吃了个肚子圆鼓鼓。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我又想起,大概在我六十岁时候,上高中的孙女带回来一捧新鲜荔枝。我当时在井边,刚打上来一桶冰凉的水,把荔枝冰进去,过一会捞出来吃。我第一次吃到这个果子,一股清甜,我吃的笑眯眯的。
我总是恨老伴贪吃。零食,瓜果,她都会藏起来,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享用。那年代,吃的少,虽然她年龄很大了,孙子孙女都好几个了,好吃的也还是藏起来自己吃。渐渐的,她年纪大了,记性变得不好,藏起来很久都忘记吃。很久不登门的孙子,她终于舍得拿出来一些,结果一看却早已腐烂了。她还爱吃肥肉,说只有肥肉解馋。后来得了高血脂,医生说再不能吃了。我虽然管的很严,不给她吃。不过,她还是会偷偷吃几块。
可是如今想起来,难道她那样真的不好么?人活着,走到最后,总会惦记食物的味道。
我很想吃羊肉面,也很想吃荔枝。可我不能吃,吃了就会拉,我已经不能自理,我不愿意儿女们嫌我脏。也不想儿女们看到我的身体部位。
第六夜,我听着墙上时钟的滴答声,闭上了眼。我的灵魂却自由起来,它游荡在我的田里,我的麦苗是那么青葱。隔壁那块地上,有一个坟头,是村里曾经跋扈的那个村长的。我对着他的坟头说:你这混蛋,作恶多年,害死了我家那么多人,却得享善终,居然得了急病没有受罪就死了。你的子孙还这样孝敬,老天不公呐!
坟墓里却飘出一个愤恨的声音:“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的子孙孝顺了?我告诉他们我肚子疼,喊了好几年,小病积成大病,他们都没有带我去治疗。外人看过去还以为我得了急病!老天爷!再说,我哪里害死你家人,那是我的错么?我有那个能耐保住全村人么?”
我说:“那你家怎么没人饿死?全村人饿死那么多,只有你老婆白白胖胖。你是帮凶,你是罪人,你抵赖不了。我死后,将住在这块土地上,日夜对着你的坟头咒骂,诅咒你的后代。可恨你还安稳的睡在这!”
我对着他的坟头又踢又打,却不见半点损伤。我看了一下我的脚,它们渐渐溶解在暗夜的黑雾里。
忽然,我于万籁俱寂里,听到一个女婴的哭声,那哭声开始洪亮,继而越来越微弱,终至于消失,就像是眼前沉沉的黑夜吞噬了她的声音。她是谁?我有点迷茫,是我的女儿么?我第一个孩子。那个饿死在六零年的小女婴。
我那天听到几个媳妇谈话:大人没饿死,却把小婴儿饿死。他们就是心黑,不喜欢女孩,不疼爱她。估计早就想让她死了。
我无力辩驳,我确实没有尽最大努力保住她的命。那并非真的荒年,粮食都在公社里,他们打算运走。那一年,饿死的,不仅仅有我的女儿,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如今,我六天没吃了,我的胃里已经没有一粒米,我的骨头上也没有几两肉。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也要重复他们的路,饥寒交迫而死。
今夜,他们都来接我了。哥哥还是年轻的模样,他说:你怎么老成这样,比父亲还要老。母亲还是严厉的模样,忽然她笑了,她向我伸出手,想拥抱我。我从没见过她如此慈爱,不自主的向后退。。。
我睁开眼,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卧室。这是我当年亲手盖起来的房屋,这一束光也是从我当年留的一个小窗洞里射进来的。儿女们陆续来了。我看着他们的模样,忽然觉得今天我该走了。我不能因饿而死,那是太痛的记忆,埋在我的最深的梦魇里。
中午他们都去吃饭了,我闻到味道,正是羊肉面。我积聚起最后的力气穿戴整齐,走到窗前,深深的嗅着这味道,似乎回到了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看到院外柳枝发了芽,院内果树抽了条。我转过头,看着我熟悉的房间,我把两条鞋带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我把脖子往上一搁,像往常在田里拔草那样,我蹲了下来。。。
晌午的阳光正好从窗户打在我身上。
文/锦瑟
链接:https://www.yyinn.net/3087.html
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自行上传,本网站不拥有所有权,也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果您发现有涉嫌版权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www.yyinn@163.com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