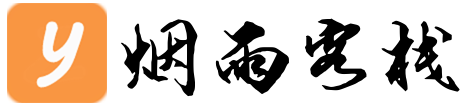从前,镰刀可是一件稀罕之物。尤其是宽扇镰刀,小到收割庄稼,大到砍柴,无一不适,庄稼人常常把它当作宝物,只是由于它过于锋利,昂贵,又常常被他人觊觎,所以一般会把它藏在唯独自己才能找得到的神秘地方。
爷爷有一把好镰刀,无论是磨得发亮的刀身,还是黑得发光的刀把,看上去都极为结实。每次看他提镰走向麦田,我就知道那镰刀可以尽情享受麦香了。印象里,六岁以前,我都没有碰过那把镰刀,因为那玩意虽然管用,但容易伤人。稍不注意就会割到手和脚,所以我只能远远地感受爷爷挥舞着镰刀,刮下一大片稻田和麦子,所带来的快乐。
当过了收获季节,镰刀的作用似乎显得更大了。秋天的黄昏笼罩在疯长后枯萎的茅草上,爷爷提镰走向它们,阵阵草香随风飘荡,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被廓清了。而我尽享着落日余霞的静谧,无意间闻到了四处新生的气息,因为来年的野草又将席天卷地。就这样,爷爷的镰刀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部分。可是每当我问及镰刀所在,爷爷那张因成年累月被风吹日晒的脸,乍然变得无比严肃起来。在那个锄头和镰刀缺一不可的时代,这更加重了我揭开镰刀那神秘力量的好奇心。
据说一把好的镰刀,需要配上结实的刀把,做工极其讲究。刀身上沿的色泽呈青黑色,则轻重有度,下口不宜偏薄,略厚为佳,耐打磨又耐修复,至于刀把,必定是用上好的油茶树桩,经过干晒定型后才可上刀。市面上其实不乏成品镰刀,但新买的总不如自己亲手制作的好,更何况用惯了的,实在无法比拟。因此,爷爷的镰刀连碰都不让我碰,也许是爷爷害怕我弄坏了他的镰刀,也许是害怕镰刀伤了我。
寻常人家如若没有一把好的镰刀,这在别人眼里看来算个可怜人,而且关系不是非常好,通常无人肯借,因为怕出了毛病,双方扯皮。如若肯借,那也只能在人家冬歇期,借用镰刀动手去山里砍柴,以备严寒。
当我度过了黄口之年,收获对我来说,渐渐成了一场场噩梦。尽管爷爷开始有意无意地将镰刀授予我,但我已十分不爱劳动,尤其是顶着骄阳下田割稻,那飞蛾和打屁虫委实让我心烦意乱。手提小镰刀可以尽情释放心中的不满,但刀口上的锯齿常常因为不够锋利而致使我事倍功半。我寻思以此为偷懒的借口,可别家孩子都干得起劲,怕惹来笑话,总不能在这方面输丑,于是心神不宁地割稻。爷爷看我犯了大忌,怀着多年不变的心思教我正确的站姿,如何使用小镰刀,仿似只要我持之以恒,学到了要领,他就会马上把他手中的镰刀传给我。八月的天空,万里无云。设若十年、二十年呆在这大地上,那么未来一定不会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
爷爷看出了我的心思,遂让我递禾即可,免去了长时间弯腰的疲乏。每次一推打谷机,我都是最卖力的那一个,因为我总想凭借最后一丝力气,尽量把打谷机往前挪一点,好快点儿收割完稻田的谷子。可是过了这一亩,又是下一亩,似乎永无止境。
记得这天傍晚,爷爷那一贯会藏起的镰刀,公然摆放在窗台。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将镰刀藏了起来,如此一来,明天出山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到了夜晚,秋风渐凉,月光洒在门前的水稻秸秆上,仿似一片触目惊心的往事。我隐约意识到那个锄头和镰刀缺一不可的时代,早已江流日下,只不过眼前这代人无力奈何罢了,但一想到起早贪黑的爷爷四处为找镰刀而焦急万分的情景,我便吓了一跳,然而睡意滋生,只在梦境中将其恢复原位。
第二天清晨,生平第一次像诈尸般弹起,不是去劳作,而是帮着找镰刀,我自知藏了镰刀,也自知没能及时将它恢复原位,但决不敢当时拿出来。那一整天,爷爷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没有流露出一丝坚毅的神情,就像父亲生前喝了酒一样对生活失去了信念。等到悔意渐浓,像乌云般将世界覆盖,我才奔回家中,从门前的秸秆里找出那把又黑、又亮的镰刀。
在一声声赞赏之下,我的悔意也渐渐消失了。不过打那以后,我便自觉肩负起为爷爷保护镰刀的责任。每当爷爷将饱食禾香的镰刀递给我,我都能从刀口上闻到汗水与幸福并存的味道,尔后把它藏在只有我与爷爷才知道的神秘地方。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寄校,不再每天为爷爷藏刀,但时常挂念着家中的这件宝物。
春去秋来,愁心似醉,这一晃,便是二十多年。
也许我们是最后经历过完全农耕的一代人,既希望记住上一代人的生活,又不顾生死地挤入城市中央,日子颠沛流离地过,却依然坚持不退,为的是有一天可以重返故乡喘一口气。当手持镰刀的克洛诺斯形象成了时间流逝的象征,死亡的封印便会开启,过于纵容的青春将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使命。
在这温饱的余年,曾经的希望和噩梦、好奇和失落,统统化身为稀里糊涂的怀旧。鬼祟的IT时代,努力把世界缩成一点,通过大数据、大信息渗透到当今各行各业领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鼓噪而进的DT时代愈演愈烈,超级强大的云计算,竟可以通过数以万计的数据处理,智能化精确推送新闻和广告。可以想象,意识都能被窥测、被计算的年代里,再想藏好一把镰刀谈何容易,而那个锄头和镰刀缺一不可的时代,当真江流日下,而眼前的任何一代人似乎都无力奈何。
乙亥年清明,我回家祭父,村庄里外看不见人影,连飞鸟都不曾站立在枝头。那个数十年来不曾见过一面的坟头,杂草乱生。我寻遍了屋前屋后,寻遍了儿时藏刀的地方,爷爷的镰刀不见了。那一刻,恍惚回到了黄口之年,恐慌和焦急如同秸秆在心中烧燃起来。杖朝之年的爷爷问我何事?这才让我想起了柴房,为了这点奇迹发生,为了从这点奇迹看到未来,我坚持扒开柴房的秸秆,希望爷爷的镰刀忽然发出亮光,或者现出那个黑黑的把手。然而,意外并没有发生,我的智慧在如此重要的时刻竟然灰飞烟灭。我坐在门前,亦如父亲生前喝了酒一样对生活失去了信念,不管谁问我什么理由,我都不愿开口。因为我相信有些东西你越找它,它越是躲着不现身。可是,那把刮下一大片稻田和麦子、连做梦都想揭开它神秘力量的镰刀,难道就这样被永远遗忘了吗?
文/邹近夫
链接:https://www.yyinn.net/3098.html
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自行上传,本网站不拥有所有权,也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果您发现有涉嫌版权的内容,请发送邮件至: www.yyinn@163.com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侵权内容。